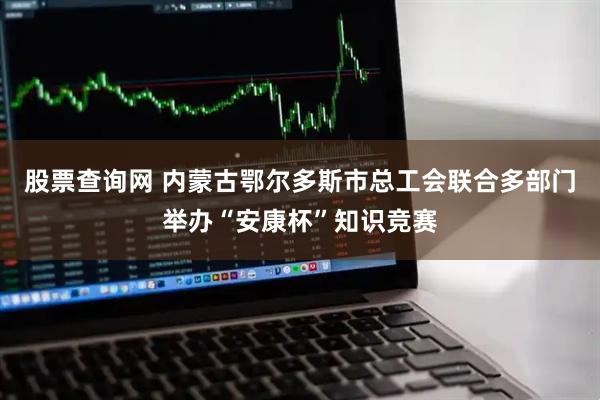如今,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一碗面,正在成为上海饮食的一大招牌。上海一些面馆前排起长队,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一头扎进街巷、弄堂,吃一碗正宗的本帮浇头面,成为深度体验魔都的方式之一。
据不完全统计,上海的中式面馆约为3.5万家。面馆数量不仅多且种类多元化,有苏式面、本帮面、兰州拉面、重庆小面,等等。面馆赛道持续细分,一碗面里如何藏着深深的城市印记?以下是上观新闻记者与文艺评论家、纪录片导演孙孟晋的对话。
上观新闻:有人说,上海是隐形的面都。上海的面食文化和它的城市气质有关联吗?
孙孟晋(文艺评论家、纪录片导演):上海自19世纪中叶以来,以港兴市,五方杂处,海派城市的风格就已体现,几批移民潮更使上海美食的多样性得以呈现。
近几十年,新上海人给这座城市又带来了新的格局。在上海,你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面食,乃至世界的风味。广而言之,本帮菜(包括面的浇头)吸取了苏帮、淮扬帮等特色,和这座城市的海纳百川的气质是贴近的。
 上海的面馆食客中,有小情侣、大家庭成员,还有许多外来游客。
上海的面馆食客中,有小情侣、大家庭成员,还有许多外来游客。
上观新闻:您认为如今林立街头的上海面馆,最可贵的基因在哪里?
孙孟晋:我一直觉得上海面馆是上海市民文化的象征,它最可贵的基因是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形态息息相关的。
它首先是一种烟火气。记得小时候一早起来,就陪着母亲到家的附近买早点,大饼、油条、粢饭糕,这和生活的记忆有关。有时候,家里也会做菜汤面,会过日子的上海人还会把前一天晚上吃剩的菜和米饭放在一起烧,我们家叫菜泡饭。这也是当年勤俭生活的一种写照。
其实,上海的面馆,包括小吃店当年都是开在沿街居民区的,它保留着老城区的肌理感。随着城市的改建,这样的一种市井风情很难长存,它的消失也是时光流逝的美好记忆。
另外,要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,快餐文化是当下一个时代的痕迹。但随着近年城市版图的重新规划,我相信儿时的生活基因又会渐渐回来。
上观新闻:伴随城市的变迁,我们如何留住记忆中一碗面的味道?
孙孟晋:记得以前在一些老城区,在过街楼底下,或者弄堂口的遮雨处,都有弄堂里的阿姨摆摊头。我每次去浙江南路淘碟,都会去对面弄堂口的阿姨摊头上吃一碗阳春面,或者大馄饨。那时的苍蝇面馆与弄堂摊头,和家里做得好的人家的小吃没什么两样,甚至更好吃。
去任何一座城市,上一辈的人都会和你讲解当年的劳动人民光顾的苍蝇面馆。上海也一样,记得老卢湾的面馆的面汤大多是浓油赤酱的,因为出租车司机大热天需要补充盐分。
还有,老城厢里苍蝇面馆的代表——胖子面馆,就开在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里,这条小马路直到后来拆迁时,都还没有换上抽水马桶,这种世俗生态就是上海的老味道。但是这样的苍蝇面馆搬到商场里去,你会发现从味道到气息都大相径庭了,这是永远在调和但难以真正解决的矛盾。
上观新闻:上海的面馆文化,可以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又一个标志或符号吗?
孙孟晋:讲上海的饮食文化必定要讲到上海面馆。上海人喜欢吃面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其实,没有什么角度比饮食文化更适合作为切入点来探讨上海的城市发展。上海出过大量的文化界的“老饕”,比如严独鹤、唐大郎、邵洵美等等,也许应该这样讲,民国时期不会吃的文人几乎没有。
近年来,随着对上海城市海派风味的复兴与重视,关于饮食的怀旧成为不同年龄的市民与游客关心的话题。人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情趣。恢复市井气的面食文化、小吃文化,都可以看作上海这座摩登城市的一个缩影,或者一种文化标志。
 市民在上海的小面馆里排队吃面。
市民在上海的小面馆里排队吃面。
上观新闻: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时代的快餐文化。在快节奏的社会,大众仿佛进入了一个“标准化”的餐食时代,其实商场里的餐馆、面店很多都是连锁化的。
孙孟晋:任何一样东西标准化了,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千姿百态。快餐文化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,它对于美食以及延伸的意义,尽管是中性的,但对于慢生活是有悖的,毕竟生命不能永远处在加速度里。
上海的面食是极其丰富的,它需要慢慢地品尝。你在匆匆赶路的停留中,一碗面是有着瞬间的快感,但在面馆周边闲逛的生活的意义,也将你浸润其间。
以阳春面为例,它是上海人曾经那么光鲜而有质感的记忆。当年一碗上佳的阳春面并非寡淡而简单的东西,面馆的师傅会用猪大骨或者蹄髈来调一大锅汤。它是简朴生活的一种印记,但它绝对讲究,和上海市民生活是对应的。
总而言之,只要崇尚个性,崇尚工匠精神,一切生活的美好都会迎面而来,这不只是儿时的记忆。
(文内图片来源:除注明外,均为作者拍摄、受访者提供)
 海报设计:邵竞
海报设计:邵竞
大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没有了
- 下一篇:股票查询网 中国通号:董事张权因个人原因离任